湖北文艺名家—於可训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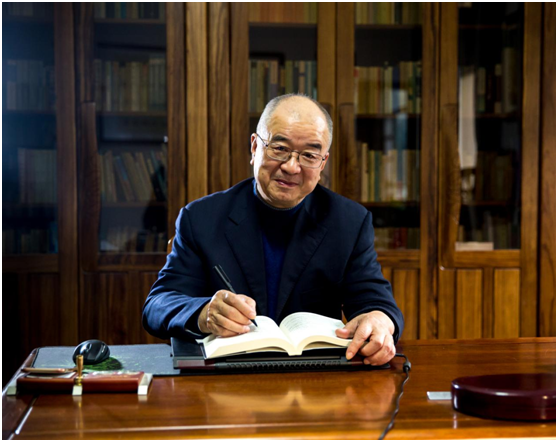
於可训,男,1947年3月生,湖北黄梅人。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,博士生导师。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。曾任中国写作学会会长,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,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,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,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,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,《长江文艺评论》等刊物主编。著有《於可训文集》(10卷),中短篇小说集《乡野传奇集》《才女夏娲》《鱼庐记》《祝先生的爱情》《渔人故事集》等。
主要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集
学术著作
1、《小说的新变》,长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
2、《批评的视界》,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
3、《新诗体艺术论》,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
4、《新诗史论与小说批评》,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
5、《中国当代文学概论》,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,2003年修订版,2009年第三版
6、《当代诗学》,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
7、《当代文学:建构与阐释》,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
8、《小说家档案》(主编),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
9、《中国文学编年史•现代卷》(於可训、叶立文主编),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
10、《中国文学编年史•当代卷》(於可训、李遇春主编),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
11、《“我读”文丛——当代文学新秀解读系列》(主编),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。
12、《对话著名作家》(主编),河南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
13、《王蒙传论》,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
14、《新诗文体二十二讲》,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
15、《新世纪文学论集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
16、《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史》,(台湾)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
17、《中国大陆当代诗学》,(台湾)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
18、《写作》(於可训、乔以钢主编),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
19、《文学批评理论基础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
20.《於可训文集》(10卷),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。
文学作品集
1、《乡野传奇集》,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
2、《才女夏娲》,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
3、《鱼庐记》,湖南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
4、《祝先生的爱情》,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24年版
5、《渔人故事集》,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5年版。
松竹梅与中国文化风骨
於可训
松、竹、梅是中国人所喜爱的自然事物,也是中国人所推崇的一种人格精神的象征。这种人格的象征物,既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体现,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。
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将自然人化的传统,这个传统,既可能源于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验,又显然与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的影响有关。中国古代哲学讲天人合一,物我同一,所以自然事物就容易被人格化。中国古代文学重托物言志,以物喻人,所以用自然事物作文化和人格的象征,也就成了一种修辞手法。这种人格化的自然事物,在植物界,最著名的莫过于松、竹、梅、兰、菊这五种不同科目的植物了,松、竹、梅被称为“岁寒三友”,梅、兰、竹、菊,被称为“四君子”,已是尽人皆知的常识。此外,如《诗经》中的荇菜、屈原笔下的香草,还有如桃、李、荷、桂、牡丹、杜鹃、杨柳、藤蔓等花草树木,以及与之有关的山石泉林等,也都被古人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涵和人格精神。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抒情文学作品的情感诉求和思想意蕴,大多是通过这些物象或由这些物象所构造的意境完成的。这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文人陶冶性情、涵养人格、砥砺人生的重要参照物,古人因而大多喜欢与这些自然事物为邻,甚至视其为至亲家人。传说苏轼被贬到黄州,有个地方官去拜访他,问他一个人在这儿是否感到寂寞,苏轼指指门外说,我这儿有“风泉两部曲,松竹三益友”,何寂寞之有。他还有一句话,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”也很有名。又传说爱梅成痴的林逋终生不娶,以梅为妻,以鹤为子,所谓“梅妻鹤子”,都是典型的例证。如果算上古人为各种飞禽走兽和日月星辰、风雨雷电、晨晖夕照、长河大漠、小桥流水等自然景观所赋予的某种文化的和人格的象征意味,则古人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,真的就成了一座“象征的森林”。这座“象征的森林”同时也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,是今天需要开发利用并加以创造性转化的重要文化资源。
在这些自然事物中,松、竹、梅之所以受到人们的特别喜爱,被人们赋予了更多的美好品质和德行,并不完全是因为它们自身所具有的某种自然属性,即学者们所说的物自性,而是同时也因为赋予其意义的古人自身,也存在与之对应的文化和人格诉求。中国古人立身处世的观念,受儒、佛、道三家影响很深,就人格构成而言,既强调“入世”所需要的积极进取、正直忠勇、刚毅坚韧的品德和意志,也重视“出世”所保有的清高孤傲、淡泊宁静、飘逸萧散的情怀和意趣。这样的文化和人格诉求,正好与松、竹、梅的某些特性相对应,松、竹、梅自然就成了古人这种人格力量的化身。马克思说,“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,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”,“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,恰好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本质,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。”松、竹、梅这样的自然事物,因此也就以它们与中国文化独特的本质力量相适应的性质,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人格精神的对象物。经过了这样的一个对象化的过程,这些自然事物就进入了精神文化系统,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些重要表达意象和组成部分。这种对象化了的自然事物,又因其对象化的独特方式,往往是通过审美的艺术创造完成的,因而又与中国人的审美旨趣有关。中国人喜爱松、竹、梅,固然离不开观赏其外在形相,但更多地却是欣赏其内在品格。这种品格虽然古人对之有不同的提炼和概括,但如松的枝干如铁、岁寒后凋,竹的中空外直、宁折不弯,梅的凌霜傲雪、玉洁冰清等等,却是自魏晋以降中国人所推崇、所提倡的一种风骨。这种源于先秦儒者“浩然之气”的风骨,在中国古代曾用来评品人物、鉴赏书画,后来又用于论文,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范畴,对推动历代诗文革新,起了重要的作用。古人论人讲“风骨奇伟”“风骨清举”,论画讲“气韵生动”“骨梗有力”,论书“以风神骨气者居上”。刘勰论文,则在各体文章风格中,独标风骨,他说:“怊怅述情,必始乎风,沉吟铺辞,莫先于骨。故辞之待骨,如体之树骸,情之含风,犹形之包气。结言端直,则文骨成焉;意气骏爽,则文风生焉”。他因此提倡一种“风清骨峻”的文章风格。凡此种种,由评品人物到鉴赏书画、谈文论艺,风骨都是一个普遍运用的标准。可见,风骨不是某个艺术门类的概念,也不是某些个人的偏好,而是一个普遍适用的范畴。宗白华说:“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‘人物品藻’之美学, 美的概念、范畴、形容词, 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。”这种从“人物品藻”出发,“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”,而后遍及整个艺文领域的美学,不啻就是中国文化的代名词,因而风骨既是一个美学范畴,同时又是一个文化学范畴。在审美领域,它是一个极高的标准,在文化领域,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体现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中国人对松、竹、梅的喜爱,既是一种审美鉴赏,同时也表现了一种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。
由松、竹、梅这些自然事物所体现的风骨,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,首先是出于中国人遵循天道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,所谓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”是也。故古人主张养“浩然之气”,培植一种强旺的内在精神,以应对人生的各种艰难困苦,成就人生的各种事业,这是中国文化讲风骨的精神源头。但是,当这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在现实中遭受挫折、与现实发生冲突而又无力抗争、不愿屈服时,也有转而以一种遗世独立、超然物外或纵情山水、放浪形骸的态度对待现实者。这固然也被古人视为一种骨气或风骨,但在现代人看来,却是一种比较消极的人生态度。虽然历代都有这样的隐士或逸人,但魏晋时代的士人似乎于斯为甚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风骨又有性质上的区分。
与古代不同,现代中国人所讲的风骨,一方面固然有古代文化的精神传承,另一方面,也有现代文明的影响和现代精神的浸润。这种现代意义上的风骨,往往与人的主体性有关,就个体而言,是个体的主体性,多表现为个体的人格或个性,就群体而言,则多为一个民族的主体性,即通常所说的民族性格或民族精神。在现代革命历史和今天的建设实践中,也指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和革命精神。具体到一个革命者和共产党员来说,风骨是对理想信念的坚守,是百折不挠的意志,是一心为公的品格,是光明磊落的胸襟,是清正廉洁的作风。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,涌现出了无数有风骨的革命者和共产党人,他们是鲁迅所说的民族的脊梁。正是有这样的民族脊梁的支撑,中华民族在经历了百年沧桑,通过血与火的革命摆脱了屈辱和痛苦之后,才成了今天这样的一个可以扬眉吐气地讲风骨的民族,也是一个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有风骨的民族。
在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,松、竹、梅作为一种自然事物,其形态和习性虽然没有多少改变,但人们赋予它们的涵义,却在不断发生变化。这种变化最明显的是古今的差异。今人欣赏、赞颂松、竹、梅,固然也重风骨,但却赋予了新的理解和阐释,且大多与革命者和革命精神有关,如陈毅的诗“大雪压青松,青松挺且直。要知松高洁,待到雪化时”,陶铸的散文《松树的风格》,再如革命歌曲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》《红梅赞》,现代京剧唱段《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》等等,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篇名曲。这些被赋予了革命的文化涵义和革命者的人格精神的松、竹、梅形象,对今人的激励作用,无疑与“岁寒三友”的形象所起的作用,是完全不同的。这同时也说明,传统文化的表达意象,需要给予新的阐释,才能对今天的社会人群发挥更大的现实作用。也才能使这种意象所表达的文化精神,得到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。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座巨大的历史宝库,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象系统,也是一片茂密无边的“象征的森林”,当我们打开这座巨大的宝库,向这座茂密无边的“象征的森林”输入更多新的精神营养,相信在我们面前,将会展开一片更为壮观的莽莽苍苍的文化绿原景象。
2018年9月4日
(载《 人民日报 》 2018年10月03日,文字略有改动)
酒事记趣
於可训
最近,我把每天中餐必喝的一顿酒戒了,年纪大了,想过极简生活,就删去了许多额外的嗜好。删是删了,但几十年来饮酒的痕迹还在,想起那些饮中趣事,又不免要生出几分眷恋,就像想着分手后的恋人,那些浪漫的情事还是不能忘怀的。
小时候见大人喝酒,觉得十分有趣。一只跟如今的迷你果冻杯差不多大小的白瓷杯,里面浅浅地装着一杯酒水,喝的人慎重地端起来,放到嘴唇边,很用心地嗦上一口,发出吱吱吱吱的叫声,像老鼠被踩着了尾巴一样,有滋有味,就想着喝酒一定十分有趣。
后来才知道,这种有趣的喝法,是因为酒少,要省着喝,但又要做足样子,装够面子,尽到礼数,才不得不用动作和声音来补足。等到自己也有了喝酒的机会,却无须如此节省,一开始便大杯浇灌,如牛吸水。
我们老家有个习俗,新谷收割上岸要举行庆祝仪式,谓之吃新。吃新的庆典少不了酒,用新谷酿酒,就成了吃新的一件盛事。大半是在有水塘的地方找一个土坡,挖一口土灶,各家把应交的新谷凑在一起,由村里会做谷酒的老人指挥一群青壮日夜忙碌,到了出酒的日子,村里的男女老少都跑出来看热闹,这时候,就该我们这些半大小子上场了。
一锅酒的酒头子出来的时候,一般都要找人试喝,试喝不是检验成败,也不是品尝口味,而是要醉人。喝醉了才有热闹看,才让看热闹的人觉得过瘾,闹过瘾了,这个吃新节才没有白过,所以这个醉人的习俗,又叫醉新。
掌作的师傅让几个半大小子站成一排,一人手上发一个写着抗美援朝字样的搪瓷缸子,把从甑子里接出来的酒头子,一个缸子里倒了大半缸,然后大喊一声说,喝。我们这些半大小子不知死活,便举起缸子,仰着脖子,咕咚咕咚把手上的酒一饮而尽。
酒头子性烈,半缸子酒下肚,起先是喉咙发烧,五内俱热,一会儿便冲上头来,双眼迷离,脸红脖粗,再以后便晕晕乎乎,站立不稳,你推我搡,拉拉扯扯,扭成一团。
这时候,围观的人便在一旁推呀,推呀,拽呀,拽呀,倒了,倒了,使劲,使劲地乱喊,年轻点的还冲进去帮忙搅和,场面顿时大乱。
等看热闹的人兴尽而归,我们这些半大小子还歪在地上呼呼大睡,直到月上中天。那时候的人大意,没有谁担心自家的孩子会出什么问题。
后来要读书上学,自然不能喝酒,再后来忽然又没学可上,没书可读,酒便像一个久别的故人,又悄悄地摸上门来。
下乡的日子少不了有苦闷,苦闷的日子少不了会想到酒,想到酒的时候又囊中羞涩,便少不了要去偷,寻常人家是偷不得的,也偷不到,于是就把目标瞄准了公社卫生院的药品柜。药品柜里有酒精,能不能喝没去想,谁叫他沾着一个酒字呢,于是便让二三“病号”去缠着医生,这疼那也疼,医生说没病还是疼,另有二三快手趁机潜进药房,军大衣里藏着瓶酒精,就像芦苇荡里藏着个新四军,谁也看不到,得手后便招呼“病号”大摇大摆地走出来。事发后自然少不了要挨批评,好在兑了水,一人一口,没喝出事来。几十年后,我喝到一种七十多度的霸王醉,跟医用酒精的度数差不多,想起当年的壮举,还陡地要生出几分豪气来。
进了工厂以后,这个偷酒喝的旧习没有尽改,这回偷的不是别人,而是师父,偷师父的酒不算偷。
我进工厂以后,开头学的是锻工,也就是打铁。我师父是个老铁匠,平生就好一口酒。师父喝酒很特别,只在上班干活前从工具柜里取出酒瓶抿上一口,下酒菜是一只用油抹布包着的卤猪耳朵,每次取出来只舔一口,把酒送下去便又包上放回原处。师父的卤猪耳朵,我们自然不感兴趣,却经不住那瓶里装的酒精的诱惑,于是就你一口我一口地偷喝起来。等到师父发现酒瓶快要喝空,一天上班,就把一众徒弟召集起来,让我们张开嘴站成一排,然后慢悠悠地用火钳从炉子里夹出一块烧红的焦炭来,笑眯眯地说,口里有酒的,见火就着,师父可能冤枉你们,焦炭可不冤枉你们。面对通红的炭火,我们都禁不住双腿发软,扑通一声,在师父面前齐刷刷地跪下,磕头如捣蒜地说,师父饶命,徒弟下次不敢。师父丢下焦炭,哈哈大笑,说,白酒又不是汽油,你怕个么事,吓唬你们的,让你们长点记性,以后不许再偷。
上了大学,当了大学老师以后,喝酒就斯文多了,但斯文也有斯文的趣味,如今想起来,也不能忘怀。
有一段时间,我常爱在人前炫耀我的一桩酒事,说我和一位老师一口气喝完了一箱啤酒。那天,我和这位老师下课后碰到一起,他说他家里没人做饭,我就邀他上我家去吃,正好,我爱人单位分了一箱啤酒放在家里,她上班去了,家里也没人弄饭。没有下酒菜,我就自己动手炒了几个鸡蛋,弄了一盘花生米,一人抓起一瓶酒,口对口地吹了起来,吹完了一瓶又一瓶,后来鸡蛋和花生米都没了,吹牛说白就成了下酒菜。我家厨房旁边就是厕所,喝胀了,就到厕所去释放一下,就这样,厨房厕所,厕所厨房,从中午喝起,直到我爱人下班,我俩把一箱24瓶啤酒喝得干干净净。
像这样持续作战的经历,还有一次。
学者陈思和年轻时善饮,有一次在我家喝酒,我请我的一个同事作陪,我们从中午喝到晚餐时分,我晚上七点有课,就中途离席赶去上课,等我讲完两节课回来,思和与我的那个同事还在对饮,我自然义不容辞,重整杯盏,继续参战,直到夜半时分方散。那一代青年评论家关系融洽,亲如兄弟,有酒必饮,饮则尽兴,家人也不以为怪。酒酣耳热处,或高谈阔论,或引吭高歌,皆属常事。有一次李洁非喝得高兴了,站在我家天井里唱了一段京剧,引得楼上楼下的住户都来观听,还以为是哪里来了一位名角儿。洁非是那一代评论家中年纪较轻的,多才多艺,素以京中名士著称,我的老邻居至今谈起这件事来还津津乐道。
跟学生喝酒就别有一番趣味。多年来,我的硕士、博士研究生毕业的时候,我都要请他们吃一顿饭,为他们送行。席间自然少不了酒。惜别的酒,容易动情,也容易醉人。有一次,我的一个博士生喝醉了,却坚持要送我回家,我当时住在一个山坡上,山坡上并排有几栋楼,这位醉博士把我送到就近一栋楼的就近一个门栋说,老师,你家到了,我说,我家不在这个门栋,他只好拉着我退了出来,把我送到另一个门栋,又说,老师,你家到了,我说,也不是这个门栋,就这样,我也不知道被他塞进几个门栋,又被他拉出来几次,最后还是我把他带回我家坐了一会儿,喝了一杯茶,再把他送到吃饭的地方。我的这位醉博士如今也当了教授,我不知道他是否也碰到过这样的醉生,他是否也被他的醉生送错了家门。
2023年12月10日写于珞珈山临街楼
(载《中华读书报》2023年12月10日,光明日报“光明网”转载)
更多作品可点以下附件下载阅读
友情链接
主办单位: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技术支持:荆楚网
地址: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翠柳街一号
联系电话:027-68880703 留言信箱:hbswlwczx@126.com 邮政邮编:430071

鄂公网安备 42010602002566号
